
王羲之 汝不可言帖拓片(局部)
笼统地说,建构当代书法批评标准体系,恐怕是一个极其困难的事情。因为以21世纪宏阔的时代视角,当代书法非常复杂。这里面,有众多的“主义”。近代百余年来,中国文化艺术界的各种思潮,有主张“全盘西化”的,有主张“引西入中”的,也有主张保持本土艺术的纯粹性,和西方保持距离的。超越门户畛域来审视,各有各的道理,都有家国情怀,都有对中国艺术未来的忧思与憧憬。书法,作为中国艺术的一个重要门类,不可能游离于“全球化”时代中西文化碰撞的大潮之外。
主张“全盘西化”、全面接受西方当代艺术思想的,我们可从某些惊世骇俗的“行为书法”、“人体书法”、“装置书法”见之。主张“引西入中”的,我们可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书坛出现并活跃了一段时间的“书法主义”、“现代书法”、“墨象派书法”等探索而见之。当然,在中国占主流的,应该说还是保持本土纯粹性的艺术主张,这也是我们当代书坛的客观现实。在“保持本土纯粹性”的旗帜下,也曾出现不同的艺术主张。有所谓“新古典主义”,所谓“流行书风”,也有什么主义也不标榜、坚持传统的艺术理念和道路——“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这是中国书法史数千年来摸索总结的道路,“融铸虫篆,陶均草隶”,“体五材之并用,仪形不极;像八音之迭起,感会无方”(《书谱》)。因此,不同的书法人,艺术观念不一样,出发点不一样,势必引来标准的不同。在传统守望者看来天经地义的,在“现代派”看来就可能陈腐落伍,应该全面抛弃。而“现代派”、当代实验艺术所玩的“书法艺术”,在传统人士看来,简直逆天,数典忘祖,离经叛道,不可饶恕。笼统地把“当代书法的评价标准”搁一块儿谈,可能没有结论。所以,我想只能把问题分开谈。
试图嫁接西方“当代艺术”于中国书法的当代实验艺术中的所谓“当代书法”,这个“当代”不是时间概念而是一个艺术形态概念,正像西方“当代艺术”的概念一样,是一个完全新兴的艺术门类。它的出现时间比较晚,它的创作观念,应该说已有一定思考和视觉形式呈现,但总体来说,新生儿还在襁褓中,因此,现在讨论其评价标准体系问题恐怕为时尚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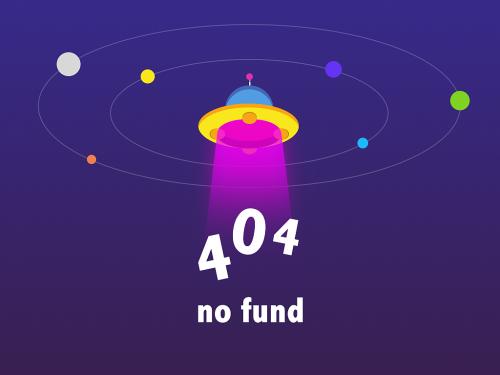
郑晓华在哥伦比亚大学举办的“从书法看中国”展览中的作品《大字大篆传统价值观系列仁义礼智信》
尝试引入一些西方“现代艺术”的观念和手法,对传统书法进行改造,由此而形成的各种“现代书法”(这个“现代”也不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一个艺术形态概念,正如西方modern art)流派,保留了部分传统书法某些元素,或采用局部夸大手法,或采用时空重叠法,或采用传统书法碎片拼贴法,等等。万变不离其宗,即降低、弱化中国书法的本土特色,提升书法的所谓“国际语言”(当然是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以求得国际艺术体系对中国书法的接纳。这些尝试(有诸多流派分支)动机当然是好的。无论在“二战”后日本,还是上个世纪80年代后的中国出现,目的都是为了使书法获得进入“世界主流艺术”的认可,尽快融入世界。在推动书法艺术的国际传播方面,这些“现代书法”诸流派确实起到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因为有西方发展成熟的“现代艺术”做参照,而且甚至在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大师中,几乎可以找到与“现代书法”十分接近的“母本”(如波普艺术、美国的抽象表现主义等),“现代书法”无论在日本还是在中国,都有较强的理论阵容。构建的理论体系,包括评价体系、标准,都相对成熟。这是谈到当代书法标准问题,不可忽略的一块。但是笔者在这方面缺乏深入研究,所以姑且引用孙过庭一句话做为托词,“既非所习,又亦略诸”。
自上世纪80年代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西方艺术思潮大量涌入中国,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但是到目前为止,西方“当代艺术”或“现代艺术”在其他艺术领域的影响,远远大于对书法的影响。究其原因,书法艺术以汉字为载体,而汉字同时还是中国文字的书面语言形式,在生活中仍然作为社会实用工具而存在。汉字这一独特的双重身份,使它在艺术领域的延伸空间受到某种制约。基于原始生活需要而产生的书法艺术形态,到目前为止,还不能摆脱原始生活功能的“羁绊”,挣脱语义传递功能的“镣铐”,脱胎换骨,蜕化为纯形式、美术类的“造型艺术”(或“视觉艺术”)。生活对书法保持了它来自母体的早在胎儿时期就定型的“表意”要求。在传统以毛笔为日常书写工具的古代是这样,近代以来硬笔取代了毛笔,现代社会电脑打字代替了日常书写,但大众对汉字书写“达意”功能的认同似乎并没有改变。因此,在美术、音乐领域,“现当代艺术”和“传统艺术”可以争得半壁江山,在书法领域,传统艺术始终占据着重要位置:书法的世界,传统的是中心,其他一切都在边缘,甚至“五服”之外。无论那些试图颠覆传统的探索者怎么摇旗呐喊,要撼动中国书法的传统,取而代之,目前来看几乎是不可能的。

北魏 鲜于仲儿墓志(局部)
传统书法经过了四千多年的培育、发展,形成了非常完备的组织肌体:理论、创作、批评、教育、鉴藏等等。它的背后,有庞大的学术体系做支撑,包括中国哲学、历史、美学等等。因此要撼动它,哪怕一点点,恐怕也是极困难的。幻想几个人登高一呼,就把历史轨道给改了,可能小看中国历史了。传统书法的批评及评价标准,虽然没有一个书法理论家,做出一全面、系统、富有哲学思辨性的总结,但在诸多书法史、书论及历代名家赏评题跋中,我们还是可以感觉到,一个强大的书法史标准系统的存在。笔者认为,中国书法史的标准是多重的,他们有时分离,有时重合,有时自言自语,有时又互相呼应。基本的存在有三个层次:历史标准、美学标准、道德标准。
历史标准,注重书家的形式语言的渊源。这一点,以清代书家梁巘观点为典型。他在《承晋斋积闻录·学书论》中说:“学书一字一笔须从古帖中来,否则无本。早矜脱化,必偭规矩。初宗一家,精深有得。继采诸美,变动弗拘。斯为不掩性情,自辟门径。”清代书家钱泳在《书学》曾说:“所书全无帖意,如旧家子弟,不过循规蹈矩,饱暖终身而已。”这些都显示了古代一部分书家对书法标准、书法基本语言的历史合法性的执着理念。没有历史渊源,即没有进入书法艺术殿堂的入场券。“殊不师古,缘情弃道”(卫夫人《笔阵图》),“任笔为体,聚墨成形”,“心昏拟效之方,手迷挥运之理”(《书谱》),自己写,写一辈子,没有“古意”,也不入流。明末清初的倪后瞻,在《倪氏杂着笔法》中,对书法的历史渊源的必要性更做了大篇幅的阐述。他说:“凡欲学书之人,功夫分作三段:初段要专一,次段要广大,三段要脱化。每段要三五年,火候方足。所谓初段,必须取古之大家一人以为宗主,门庭一定,脚根牢把,朝夕沉酣其中,务使笔笔肖似,使人望之即知是此种嫡派。从有誉我、谤我,我只不为之动。此段功夫最难,常有一笔一直,数十日不能合辙者。此处如触墙壁,全无入路。他人到此,每每退步灰心。我到此,心愈坚,志愈猛,功愈勤,无休无歇,一往直前,久之则自心手相应。初段之难如此,此后方许做中段功夫:取魏晋唐宋元明数十种大家,逐家临摹数十日。当其临摹之时,则诸家形模,时或引吾而去。此时步步回头,时时顾祖,将诸家之字,点滴归源,庶几不为所诱。然此时终不能自作主张也。功夫到此,倏忽又五七年矣。此时是次段功夫。盖终段则无他法,只是守定一家,又时时出入各家,无古无今,无人无我,写个不休;写到熟极之处,忽然悟门大启,层层透入,洞见古人精微奥妙,我之笔底逬出天机来变动挥洒。回头初试宗主,不缚不脱之境,方可自成一家也。到此又是五七年或十年,终段功夫止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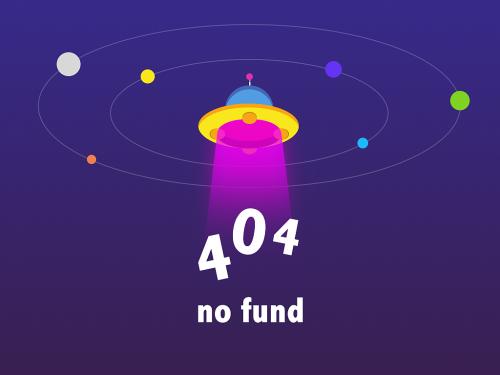
苏轼 渡海帖
书法理论中的美学标准是很独特的一套话语体系。它借用自然生命的相关概念,通过相关自然生命物象与笔墨意象之间的某种视觉“同形感”和人类艺术心理学上的“联觉”、“通感”,传递、表述中国书法所追求的某种东方艺术特有的意蕴。这方面,首开其源的大概是传为东晋卫夫人所作《笔阵图》,“善笔力者多骨,不善笔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谓之筋书,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笔阵图》使用的语例“筋”“骨”“血”“肉”,这套笔墨意象概念,后来广为书法家所接受和认同,并逐渐演绎、丰富、完善为一个完整的表述体系。如梁武帝萧衍的《答陶隐居论书》说:“纯骨无媚,纯肉无力,少墨浮涩,多墨笨饨,比并皆然。”苏轼的《论书》说:“书必有神、气、骨、血、肉,五者阙一,不成为书也。”米芾的《自叙帖》说:“学书贵弄翰,谓把笔轻,自然手心虚,振迅天真,出于意外。所以古人各各不同,若一一相似,则奴书也。其次要得笔,谓骨筋、皮肉、脂泽、风神皆全,犹如一佳士也。”《海岳名言》说:“字要骨骼,肉须裹筋,筋须藏肉……险不怪,老不枯,润不肥。”以上种种概念和判断,都立足于鉴赏者对书法笔墨形式的视觉审美感受,突出强调笔墨意象的生命意蕴与风采,有点唯美主义感觉,牵强一点,也许可以算做“美学标准”。
道德标准其实是文化对艺术的一种“嵌入”。苏轼认为:艺术与人的品格本来是两件事,但是这两件事必须搁到一块来说。苏轼的《书唐氏六家书后句》说:“古人论书者,兼论其人生平;苟非其人,虽工不贵。”黄庭坚的《论书》提出:“学书须要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致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这里都说得很明白:字是字,人是人,两者本无关联;但字要玩得好,人得有高度,否则立不住。也有一些书法家坚信:“有诸内而形诸外”,书法是心灵的图画,是人的精神的物化,两者互相关联。宋代朱长文《续书断》称:“鲁公可谓忠烈之臣也,而不居庙堂宰天下,唐之中叶卒多故而不克兴,惜哉!其发于笔翰,则刚毅雄特,体严法备,如忠臣义士正色立朝,临大节而不可夺也。扬子云以书为心画,于鲁公信矣。”清人朱和羹的《临池心解》说:“书学不过一技耳,然立品是第一关头。品高者,一点一画自有清刚雅正之气;品下者,虽激昂顿挫,俨然可观,而纵横刚暴,未免流露楮外。故以道德、事功、文章、风节著者,代不乏人,论书者,慕其人,益重其书,书人遂并不朽于千古。”明代项穆《书法雅言》提出通过“内修”“外化”,用人格外化的书法感化人心,建立移风易俗的“书教”,傅山在《诫子诗》中告诫子弟:“作字先做人,人奇字自古。纲常叛孔周,笔墨不可补。”还有著名的杨守敬《学书迩言》绪论提出“一要品高,品高则下笔妍雅,不落尘俗”,“一要学富,胸罗万有,书卷之气,自然溢于行间”,这样绝对的“人品学问决定论”,类似的论述,不胜枚举,都可看作是“道德批评”的延伸。
纵观书法史,历史标准、美学标准、道德标准,构成了中国传统书法批评的多重标准结构。它们像中国传统绘画中的散点透视,据其一点,辐射四周,而构成一个各自独立的维度。也可以交叉组合,对书法史上的人物、事件、作品进行多重组合的扫描,从而对人物、事件、作品做出多角度的描述、定位。中国文化对书法家和书法作品的普遍期待,大概是传统书法批评这一多重标准结构形成的深层社会原因。
郑晓华 中国书法家协会秘书长
(本文原载《美术观察》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