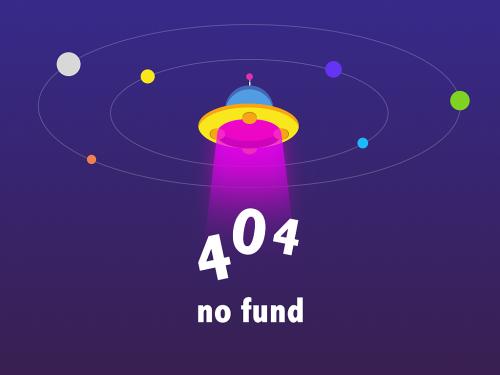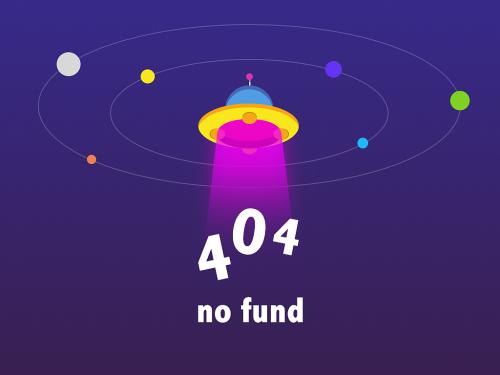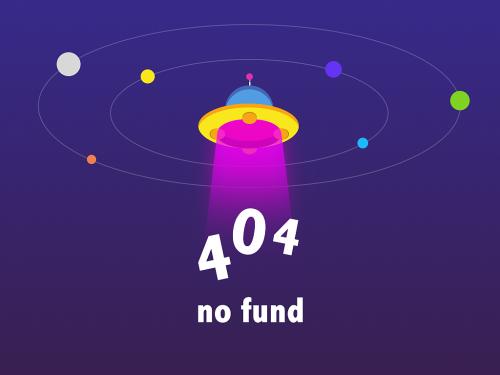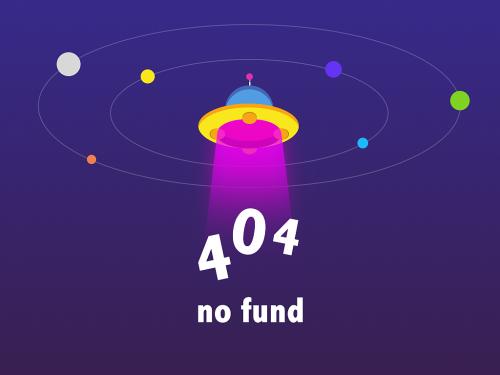毛泽东早期书法历程及其
艺术风格的形成
(作者:陶永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馆员;原载《党的文献》2012年第2期)
毛泽东书法艺术,是20世纪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的一座丰碑。近年来,随着毛泽东书法手迹的陆续出版面世,人们对毛泽东书法艺术的研究在逐步深入,关于其书法艺术风格的形成与发展流变问题,也出现了许多富有真知灼见的研究成果。但这些文章对毛泽东书法艺术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他中年以后处于风格成熟期的作品上,对其书法艺术风格的演进也偏重于大时段的宏观勾勒。笔者以为,一个书法家艺术风格的形成与演进,与其早期在书法技能上的基础性训练密不可分。因此,对毛泽东书法艺术的研究,首先应当对其青少年时代的取法对象与摩习路径进行考察,从中分析归纳出可能影响其日后书法趣向的基本原因与内在理路,作为对其一生书法历程展开整体研究的基础。本文试图从这一角度入手,对毛泽东若干早期书迹进行简要的爬梳,以期寻绎他在书法艺术实践上的方向选择与审美追求。
一
如何界定毛泽东书法历程的“早期”呢?
对前人的艺术经历予以分期,一般来说需考虑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其艺术实践活动的变迁,二是其作品艺术风格的演进,这两个方面又经常纠缠在一起并互为印证。前者常常体现为所处历史环境与其人生境遇的变化,这可以由各类文字史料(包括当事人的自述)提供佐证;后者则反映为其作品技法、意境的阶段性趣向,这种归纳更多地表现为研究者的见仁见智。关于毛泽东书法实践活动的史料,比较重要的一则来自舒同之子舒关关的回忆——1959年,毛泽东曾在济南与舒同谈到自己的书法历程:“我练字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21年以前,打下书法基础;第二个阶段是建党后到抗战爆发,由于流动性和严酷斗争环境,留下的作品不多;第三阶段是1938年到1949年,我用文房四宝打败了国民党的四大家族;第四阶段是进北京城后,全国人民兴高采烈,我的书法也就欢快飞动了。”(转引自冯都:《舒同与毛泽东的翰墨情缘》,《湖南工人报》2010年10月27日。)舒同是党内有较高书法造诣的高级干部,与毛泽东多有书法艺术上的交流切磋,因此这段话可信度较高,对研究毛泽东书法艺术的分期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那么,这“四阶段”说能否作为划分毛泽东一生书法艺术风格嬗变的界限呢?笔者以为并不尽然。原因有三:
其一,毛泽东说这段话的时间是1959年,时年66岁。对于一个书法家来说,这个年龄段的书艺水平还处于上升阶段,其书法风格的变化尚未停滞。故而,此番总结可以看作是对此前书法实践的概括,却不能涵盖其一生的书法面貌。
其二,这四个时间段,很明显是依据毛泽东个人的革命生涯或者说是参照中国近现代史分期来划分的。虽有其合理之处,但一般来讲,个人书法风格的演化很难说与社会历史的进程亦步亦趋。
其三,这“四阶段”重点讲的都是其书法学习和书法实践的外部环境。外部环境固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影响甚至决定一个人的书法行为,但具体到书法风格的形成和嬗变,它既可能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也可能取决于个人审美意识的变化,更可能是书法家书法实践过程中一种合规律、合目的而又不期而至的境界。因而,单从外部环境的角度是难以准确描述其书法艺术风格变化轨迹的。
如此看来,“四阶段”说并不能准确概括毛泽东一生书法艺术演变的进程。不过,毛泽东的这段“夫子自道”,毕竟从实践的角度道出了他前半生的书法历程,这就为研究者提供了一把钥匙。我们不妨循着毛泽东的自述,将“1921年以前”作为界定本文标题中“早期”的一个时限。
二
毛泽东亲笔书写并留存于世的文稿数以万计,这些书法资料完整地反映了他一生的书学经历和书艺嬗变。翻检1921年之前毛泽东的文稿手迹,大致有这样几类:
图1 商鞅徙木立信论(1912)
图2 离骚经(1913)
(1)结体规整、用笔精良的小楷。写于1912年的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如图1),1913年抄录的《离骚经》(如图2)以及听课笔记《讲堂录》(如下图3),是现存最早的毛泽东手迹,都是小楷字体。
图3 讲堂录(1913)
图4〔明〕黄道周诗翰册
《商鞅徙木立信论》是毛泽东交给先生批阅的作文,字体比较工整,文字结体拓宽横向而缩短纵向,体态平稳,风格古雅。这种特征在明清一些书家的小楷作品中相当常见,如黄道周的小楷(如图4)。《离骚经》当属课外抄录的古人作品,或许带有书法练习的性质,因而书写中规中矩,横平竖直,体态方正,用笔十分精到,起笔、收笔,露锋、藏锋都处理得干净利落。相比之下,《讲堂录》因为是听课笔记,书写则稍显随意一些,字形较《商鞅徙木立信论》有拉长的趋势,有的笔画(如个别撇画)比较夸张,有的则比较收敛,从而使字的结体呈现出一种极不安分的态势。在笔法上,这几件小楷书作都体现出书者对笔毫比较熟练的驾驭能力,看得出经过了严格的基础训练和他本身所具有的卓越天赋。
(2)纵向取势、楷法入笔的行楷书。现存毛泽东写于1915年的几件书迹,如致文咏昌“还书便条”(如图5),致湘生信,致萧子升信(如图6),《明耻篇》封面题字等,都是这类书作的代表。这几件书迹的共同之处,是比较明显地继承了前期小楷书字形偏长的特征,用笔的提按采楷书笔法,方折比较明显,只是由于书写速度较快,增加了一些连带。从单个笔画看,除了个别的横画稍加强调之外,其他笔画都法度严整,字形显得蕴藉含蓄了许多。同时,由于横画采取向右上扬起的笔势,又使得字形整体增添了一些挺拔峻峭之势。这几件书作,明显地体现出由小楷书向行书过渡的痕迹,因而保持了字的楷书体势,只是在用笔和部分结构中运用行书甚至草书的写法(如“还书便条”中的“新”、“至”等字),与唐代欧阳询(如图7)、宋代黄庭坚的行楷书颇有契合、相通之处。
图5 还书便条(1915)
图6 致萧子升信(1915)
图7〔唐〕欧阳询思鲈帖
(3)字形横拓、用笔圆转的行楷书。从1917年到1919年间,毛泽东的书迹又呈现一种新的面貌,一改先前结体的纵向取势,转而取宽疏扁平的横向态势。这类行楷书根据其书写时使用笔锋的深浅,又可分为两种:
一种以1917年为萧子升《一切入一》写的序(如图8)、1919年致黎锦熙信(如图10)为代表,用笔较深,用力均匀,转笔圆润,在结体上更注重横向笔画的平行等距,因而呈现出如汉代简书(如图9)那种介于隶楷之间的结体风格,又明显取法了唐人褚遂良《阴符经》(如图11)的笔势。
图8 一切入一序(1917)
图9〔西汉〕居延简书
图10 致黎锦熙信(1919)
图11〔唐〕褚遂良阴符经
另一种以1918年致罗学瓒信、1919年致舅父母信(如图12)为代表,用笔较浅,锋颖外露,用笔疾速,转折并用,笔画效果与宋徽宗赵佶的“瘦金书”(如图13)略有相似。
(4)字势连带、笔锋外拓的行书。这类书迹以1920年9月致萧子升信为代表(如图14)。与前一阶段平稳工整的结字风格迥然不同,字形抑左扬右,似又回到1915年之前那种结体的习惯。而用笔的提按转寰与笔画的连带变化,则又更显丰富成熟。同时,通过强调左下和右上两个方向上的笔势外拓,不仅增加了单字的动态,而且又在通行与通篇的整体气息上保持了连贯。这篇书作,在结字特点与整体风格上与宋代苏轼的行书(如图15)有明显的契合、相通之处。
图12 致舅父母信(1919)
图13〔宋〕赵佶瘦金书
图14 致萧子升信(1920)
图15〔宋〕苏轼李太白诗
(5)结体雍容、行笔内敛的行书。在1921年1月致彭璜的信(如下页图16)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在这一时期书法摩习的另一种尝试。这篇书作似用比较粗短的羊毫或者秃笔写就,其中锋运笔特征明显,书写时按多提少,行笔短促,又与前一阶段笔画向外拓展的习惯有所不同。从字形看,以紧密内敛为特征,风格厚重沉稳。在章法上则字字独立,有意连笔断的从容裕如。从整体来看,显然与唐代颜真卿《祭侄文稿》(如图17)沉郁迟涩的气息相通。
图16 致彭璜信(1921)
图17〔唐〕颜真卿祭侄文稿
(6)造型典雅、运笔灵动的行草书。1921年致杨锺健信(如图18),是这一时期毛泽东行草书作的代表。细看这件书迹,其点画姿态多变,轻重得当;用笔流畅自如,收放活脱;结字方圆并举,灵动有致。在体势与用笔上,这篇书作与唐人孙过庭的《书谱》、贺知章《孝经》(如图19)等小草书的韵味如出一辙。与之前的书迹比较,可以看出这篇书作无论是在用笔、结字还是在行气与章法上,都是对先前几种类型书法特征的一个总结与提高,而且它克服了前几个阶段中为了强调某一方面的特征而出现的些许“习气”,将书写技巧与结字法则结合得比较圆熟,令人感佩。
至此,我们对1921年之前毛泽东的部分书迹进行了排比解析。可以说,以致杨锺健信为标志,毛泽东书法在这一时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如果将考察的目光再往下稍加延伸,我们还可以发现,在此后几年时间里,毛泽东书法在用笔的提按转寰、结字的偃仰收放等方面变化不大,再没有在某个方面进行特意训练的尝试。如1922年致欧阳振垣信(如图20),1923年致光亮信(如图21),除了在书写方面稍稍草化了些之外,其他如点画形态、结体特征都与致杨锺健信差别不大。这就是说,从1921年之后至少到1923年间,毛泽东的书法风格进入了一个相对成熟稳定的时期。
图18 致杨锺健信(1921)
图19〔唐〕贺知章孝经
图20 致欧阳振垣信(1922)
图21 致光亮信(1923)
三
从以上排比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毛泽东青年时期的书法实践,遵循了“小楷—行书—草书”这样一条路径。就汉字的应用而言,行草书是最方便实用的字体。而在传统的书法学习与训练中,楷书被看作是行草书的基础,因为“图真不悟,习草将迷”(孙过庭《书谱》语),很少有人能跳过楷书阶段的训练直接学习行草书的。因而在旧时的教育课程设置中,毛笔小楷一向被强调为学生的基本功,生长于那个时代的毛泽东自然也不例外。从前面列举的书迹看,学生时代毛泽东的小楷书结体古拙,用笔熟练,这为他后来的行草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依时间顺序考察以上所举毛泽东的书迹,由楷而行、由行而草这样一条演进路径十分清晰。
第二,毛泽东在早期书法研习上表现出十分明显的主动性、针对性与包容性。从《离骚经》那样一丝不苟的习字作品看,毛泽东在求学阶段对书法有着强烈的兴趣并进行了严格的训练。而在此后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他的书法面貌几经变化,甚至在一年当中也有不同特点,并且每次变化都能体现出对传统书法特征的借鉴,表明他在书法上已经在有意识地从传统书法中汲取养分。同时,这一时期,毛泽东的书迹在字势的纵与横、用笔的提与按、收与放,在结体的内敛与外拓、疏阔与绵密上,经历了多次的交替与反复。这表明,毛泽东在向传统书法学习取法过程中,带有比较明显的“纠偏”意识,力求通过对不同类型书体的尝试,去修正前一阶段书体中那些已形成定势的结体和用笔习惯。正是在这样的反复实践中,毛泽东得以涉猎各种风格迥异的书法资料,并以兼容并蓄、为我所用的态度取其精华,达到心手相称的境界。
第三,这一时期毛泽东的书法呈现出继承重于创新、传统重于个性的特征。虽然尚无明确的史料证明毛泽东在学习阶段临习过哪些碑帖,但从上述列举的每篇书作当中,我们都能看出它们与传统书法特征的契合。这显然是有意学习揣摩的结果。另一方面,这些书作都是毛泽东在日常学习工作与书信交往中留下的,属于实用性的文书,并非纯粹意义上的书法创作,因而其中多少带有一些个性鲜明的痕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个性化的痕迹趋于淡化,运笔结字的习惯和技法越来越向着传统书法的规律靠近。也就是说,这个阶段毛泽东书法更多地表现出对传统书法的揣摩与取法,并达到了与传统书法的审美特征高度契合的程度,但尚未形成个性鲜明的独特风格。因而,将这一时期毛泽东的书法称之为“打基础”、重法度的阶段,是符合实际的。
毛泽东是天纵之才,他的书法
可横扫千军,无人匹敌!
我们来看看毛泽东年轻时候的字迹:
你原以为,毛主席年轻时的书法就很潇洒奔放。
现在,你可能小失望了。
我们继续看:
慢慢的,主席书法逐步成长。
直到青年时候,主席的书法味道愈加浓厚。
毛泽东的书法是信笔成书、不拘俗套的。
书法艺术的本质,是表现个性,故而透过一个人书法的结体、运笔、书写习惯,我们大致可以窥见其性情特征。一般来说,喜欢狂草的人,通常性情奔放、浪漫;而喜欢写正楷的人,则严谨刻板。顿挫分明的字体,可以看出一个人为人刚健有力;而汪洋恣肆的书法,则折射了一个人豪放不羁的情怀。
毛泽东《清平乐·会昌》
毛泽东的书法不可学,是因为毛泽东是天纵之才,其书法洋溢着无与伦比的才气、豪气、灵气、霸气、神气,令人叹为观止,敬之仰之,绝非常人可以驾驭。
欣赏毛泽东书法,我们既能感受到他的龙蛇飞舞、大气磅礴、豪放酣畅的书法艺术之美,又能感受到他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睥睨天地、独领风骚的伟人风范。
毛泽东书王昌龄《从军行之四》:“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斩楼兰誓不还。”
就书法艺术而言,最能代表一个人艺术成就,并能最好表达艺术家个性的,莫如草书。毛泽东就选择了最能体现其浪漫豪放情怀的草书,即使其行书也带有草意。
毛泽东的草书,下笔顿挫分明且颇有力度,行气十足,虽师法怀素、张旭和黄庭坚,却更加大气和酣畅:不论从结体章法上,还是运笔上都极其狂放和洒脱。
毛泽东《七律·长征》
另外,毛泽东的书法,既有棱角分明的狂放书风,也有舒缓写意的抒情书风,前者如《七律·长征》,后者如《采桑子·重阳》,其中可以看出他能屈能伸的政治家本色。可以说,毛泽东的书法与其诗词一样,都成为他伟人风范的绝好写照。
毛泽东《采桑子·重阳》
关于毛泽东的性格,他自己有一句非常经典的概括——虎性与猴性的统一。孙猴子最具造反精神,老虎有山中之王的霸气,毛泽东身上同时兼具霸气和造反精神,这种性格在毛泽东的书法中也得到了很好的彰显。造反精神使毛泽东在书法创作中勇于创新,敢于“破格”,时出新意。
毛泽东的书法不物成规,有着极其鲜明的创新意识和鲜明的个性特征:他师古人而不拘成法,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推陈出新,独领风骚,从而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毛字”、“毛体”。
霸气是毛泽东书法中的一股雄放之气,气势咄咄逼人,汪洋恣肆,纵横捭阖,节奏铿锵,一泻千里。
如果站在“视觉冲击力”角度观赏,其“形式艺术”的动感魅力,可以横扫千军,无人匹敌。
毛泽东与书法
(作者:柳 栋)
1963年3月5日,毛泽东同志手书的“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公开发表,这幅题词震惊了中国书坛,令无数人赞叹。由此,他“非行非草”的书法又一次被世人广泛认知,进而被加冕为“毛体”。这是中国书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个重大事件,影响深远。
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毛泽东作为一代雄才大略的历史伟人,我们更多了解的是他作为革命家、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的一面。正由于政名太高,却掩盖了他在诗词、书法等领域的不凡成就。其实毛泽东在书法领域的成就依然非常之高,与历史上任何一位书家相比,毛泽东雄浑豪放、气势如虹、风格独特的书法艺术本身,以及他对中国书法艺术振兴、复兴的巨大贡献和所取得的卓越成就,至少在现阶段的中国书法史上,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个评价既不过分,也不夸张,因为毛泽东做到了“是真书家自风流”的大境界。
毛泽东《忆秦娥·娄山关》
世人对毛泽东书法“毛体”的认同是毋庸置疑的。但长期以来,一些人把毛泽东的书法定位为“狂草”的误读也是根深蒂固的。因为这个误读,某种程度上模糊了对中国书法书体的界限。书体的区分主要是以基本形制来划分的,而非以笔墨和气势来区分。以楷书为体,草书为用,谓之“行楷”;以草书为体,楷书为用,谓之“行草”。综合来看,毛泽东书法的准确定位应该是“行草”,而非“狂草”。代表毛泽东书法艺术的最高成就的作品有两幅:一是取大草气势的行草代表作品为《忆秦娥·娄山关》,可竞秀张旭、怀素;二是取小草气势的行草代表作品为《沁园春·长沙》,可比肩王羲之、颜真卿。这两幅诗书合璧、书诗双绝的作品,是书家书写形式与内容完美统一的扛鼎之作,可雄视古今,为书法艺术上的神品之作、巅峰之作,实则代表了中国书法发展的最高水平,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毛泽东《沁园春·长沙》
世界上所有的文字包括四大文明古国的文字,唯有中国的汉字因其特有的结构和美感而被称之为“艺术”,中国书法则是世界上独有的视觉和造型艺术,是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毛泽东的书法坚持中国文化和书法的本源,在保持中国汉字字形完美姿态的基础上进行继承与发展,用独特的用笔、笔法、章法开拓创新书法艺术,纠正消除了草书过度浪漫(包括随意改变字形)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为中国书法开拓创新奠定了前进的正确方向,功不可没。毛泽东书法之所以产生巨大影响和魅力,还在于他坚持民众的审美倾向和应用需求的“人民性”特征。他的字虽然是书法艺术,但民众喜闻乐见,是无论什么人都认可的中国字,不生僻怪异、不矫揉造作、不故弄玄虚,更不是连中国人自己都不认得的字,完全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民,这是值得思考和发扬的。因此,毛泽东对中国书法发展的贡献是巨大的,他是继王羲之、怀素等书家之后,对草书遗风传承开拓、发扬光大的书法巨人,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上树立了一座巍峨的高峰。
毛泽东《卜算子·咏梅》
毛泽东书法的成功,依然没有脱离继承传统——探索创新——形成风格的基本轨迹和客观规律。他书法的根基仍然是楷书,初学欧阳询,吸收颜真卿和魏碑,经历了由楷而行,由行而草的书法必经过程,严谨地继承了中国书法艺术的传统,实现了从“有法”到“无法”的境界。特别是他广泛研究历朝历代书法法帖,尤其对“二王”、孙过庭、怀素等大家书帖反复临写、品阅,对书道谙然于胸,在行草书上取得了卓越成就。
毛泽东书王之涣《凉州词》
书法表面看是在写字,实则是在写书家自身的阅历、学识、修养,以及对人生、国家、世界和宇宙的认识、思考和感悟,这种“道痕”对一个书家书风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也决定是否能成为大家的重要因素。毛泽东青少年时代主要在南方学习、生活和革命,南方的地域文化根基,造就了他的清秀、细致、睿智。中年时期,毛泽东又在陕西、甘肃、宁夏等地战斗,尤其在西北“韬光养晦”的峥嵘岁月里,成就了他的豪放、粗犷、豁达。两者结合在一起,无论做人做事,还是做学问,都有不可低估的影响。特别是毛泽东在西北的历程恰恰是他各方面走向成熟的重要阶段,使他对这片土地产生了深厚的感情,这个经历不仅对他的革命生涯具有重要影响,也对他书风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延安时,他虽然日理万机、决胜千里之外,但仍时常阅法帖,一套晋唐小楷一直带在身边。也正是西北的特殊经历和难舍情结,毛泽东后来所书的《清平乐·六盘山》《凉州词》;题写的《甘肃日报》《青海日报》《宁夏日报》等墨迹,都是精气神十足的精品之作、上乘之作,笔端凝结和流露着对西北的特殊情缘、情结。
毛泽东《清平乐·六盘山》
除书法艺术本身之外,毛泽东自身独特的性格、深厚的学养、深邃的思想、传奇的经历,特别是作为国家领袖的心理定势、伟人气质……这些书法之外的因素,也成就了这位旷世奇才的书法巨匠,更是历史上任何一个书家所不能完全具备的,同时决定着他们在书法艺术上不好超越毛泽东。因此,要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书法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写书法更不是简单地形似和技法的问题,需要我们学习很多东西……引申到书法艺术上,亦为同理,那就是“字外功夫”。
毛泽东不是行伍出身,但他却指挥千军万马打了上百次战役、战斗的胜仗,被列为世界著名军事家行列。这与其写书法也是有关联的。因为写书法尤其是行书、草书和行草书,本身在书写时行笔结体、章法布局的过程中,就如同在排兵布阵、调兵遣将、指挥打仗。如果以此来解读毛泽东不是行伍出身,却怎么懂带兵打仗之道?统率千军万马打胜仗?某种程度上会找到答案的渊源之一。
中国书法艺术是我们的国粹之一,需要无数仁人志士不懈努力来继承发扬,探索创新,为之奋斗。毛泽东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之一,他把至善至美、至圣至尊的中国书法艺术留给了中国和世界,成为一位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书法巨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