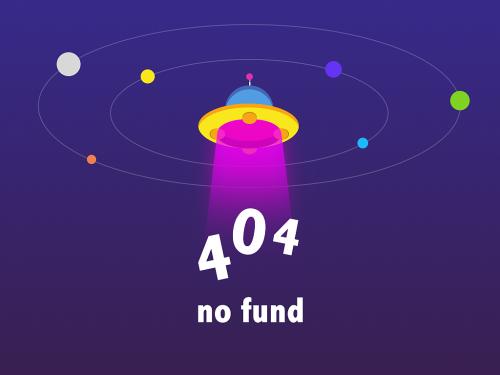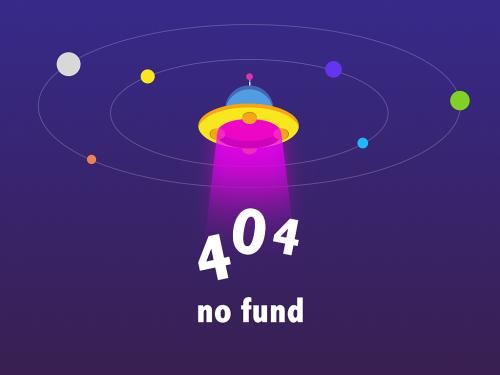刘一闻、鲍贤伦对话
近些年来,海派的书法,包括海派书法的研究,都是当代书法界的一个热点。海派艺术作为一个时代特有的产物,在艺术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包括了吴昌硕、沈曾植、曾熙、沈尹默、吴湖帆、白蕉、王蘧常、谢稚柳、来楚生、方去疾等一大批在艺术高度、市场行情上双丰收的艺术家。它的形成、发展以及在艺术市场上的表现,都令人琢磨。此前,刘一闻和鲍贤伦在山东展开一场关于海派书法的对话,管中窥豹,本期专题选取关于海派从萌芽到成熟的分期、碑帖融合的创作观念、艺术与市场的关系等几个角度,希望“可见一斑”。
沈曾植 杜甫诗 行草书 钱君匋藏于“众美抱华——钱君匋的艺术世界”中展出
海派书法的分期
鲍贤伦:海派书法的分期问题,要搞明白“海派书法”概念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当这些艺术家在世时,不存在海派书法、甚至海派文化这样的概念。海派既不是一个区域的名称,也不是一个流派的概念,是一种特定时期的文化现象。今天我们谈到海派,是对过去某一时间的追忆,是我们作为后人“给出”的一种看法。
海派文化是旧学养积累的成果,是江南文化和欧美工业文明结合的产物。随着观念和视野的拓宽、社会进步、市场逐渐打开,使上海成为一个兼容并蓄、开放多元的艺术地域。我们现在分期,从年份上或是类型上都是一种分期方式,但无论如何分,都把吴昌硕、沈曾植、曾熙、李瑞清这批人作为早期代表,他们在年代上更早一些,旧学养也更深厚一些。沈尹默、吴湖帆、白蕉等为中间时期代表,后期的代表有王蘧常、谢稚柳、来楚生等,由于后期的下限比较难确定,一般以方去疾为界。每个时期,海派书法的代表人物都有10余人。
从本质上来说,“海派”不是一个流派的概念,最大的特征就是兼容并蓄。海派是特定时代条件造成的,“海派”之前没有,之后也不会再有,因为现在发展的机遇不再特别集中上海,各地的人都可以有所作为。
刘一闻:对海派的界定的确是一个蛮复杂的话题,从地域性讲、从风格上讲都很难作出确切的定论。海派的叫法,是后人在回顾历史总结前人艺术创作时提出来的概念。海派的分期,学术界也有这么一种说法,就是分前期和后期。所谓前期的下限到吴昌硕,上海博物馆在陈列书法和陈列绘画的时候,把吴昌硕作为清代最后一个艺术家来定位。后海派习惯上从沈尹默开始,这是大家都比较认同的。如果我们要进一步研究的话应该还可以分得细一点的,比方说被确定为前海派的人物可以追溯到从上海开埠,一直到1927年吴昌硕去世,这是一个大概分段。1949年以后,则以沈尹默、白蕉为代表。沈尹默、白蕉和潘伯鹰为后海派的最初代表人物,来楚生、王个簃和王蘧常这是第二层的,这不是以年龄先后而是以去世的早晚分,这么分我觉得比较客观。再往后还有谢稚柳、唐云等。再之后是胡问遂、任政、赵冷月跟方去疾。
上海的书法创作至今为什么很难做到脱颖而出,是因为前面的名家太多、“枷锁”太多,这个现象会不时地制约创作上的自由性和想象力。
吴昌硕 集《石鼓文》对联 天一阁博物馆藏
海派书法碑帖融合现象
鲍贤伦:在海派书法中,我们一直忽视了康有为的影响,他是碑学的一号人物,并且在上海待过一段时间。
碑派在早期海派中占据主导地位,到中后期,碑学的实践者开始有所偏颇。上海的开埠产生了另一种可能,碑帖对峙变得没有那么水火不容。如沈曾植,他到底学碑还是学帖?我有充分的证据把他列为碑学一派,他对六朝、二爨下了很大的功夫,不然他的盘旋翻腾的笔致无法形成;他学黄道周和倪元璐学得非常好,晚年又学王献之、李世民渐渐又变成了帖学一派。沈曾植的实践开始消融碑帖的壁垒,他的“碑味晋韵”四个字足以说明一切。
时代发展,碑学的局限性渐渐暴露,加上沈尹默的帖学实践功不可没。沈尹默由唐入晋,借助于照相技术、日本的印刷术,他看了米芾、二王的高清印刷品,对帖学的笔法有了一个清晰的判断和深入实践。有人认为,白蕉写得比沈尹默更好,是晋人书法的代表,在信札体等方面,白蕉确实更为出色,但并不能改写中国近代帖学发展的历史,也不能动摇沈尹默的历史地位。
在当时的上海,帖学实践者和碑学实践者相互共存,原来学碑的人后来都开始接触帖,写帖的人也并不无视碑,在理论上,碑帖兼容几乎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只是在实践中有所侧重而已。碑帖的二元结构,被新材料的发现打破,简牍书和敦煌文书的发现,沈曾植等人马上将其作为取法的对象。西北汉简既与帖相关,也有碑有关,最早的实践者来楚生、钱君匋,邓散木也有所涉及,依旧是在上海。观念的开放和学术的立场是紧密相关的。
帖学在上海复兴,是否有某种必然性?我觉得有理。上海是吴越文化,帖学经过沈尹默的实践和推动,有很好的土壤,这是一个文化现象;加之上海的市场,受众并不仅仅只有上海,还有很宽阔的海外市场,这使得上海的艺术实践多样化,像沈曾植这样的人物,他们的市场情况非常好。现代文明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古代时,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艺术氛围和风气,虽然交通发达之后,很难进行区域性的分析,但不能说本地区的民众在文化基因上就没有倾向性。
刘一闻:碑和帖在后海派的表现样式上,似乎是碑的痕迹渐渐退去而帖的痕迹渐渐凸显。从大处讲,这也可说是一个循环转变重复的社会现象,它不仅反映在社会生活中,同样也反映在艺术上。比如说帖学从开始出现,一路上强大无比,但是到了明代中期以后,尤其是到了明代后期至清代初期,出现了五位号称奇崛书派的代表人物:张瑞图、倪元璐、黄道周、王铎和傅山。这个群体的出现,无疑对当时书坛形成了强烈冲击。然而即便是这样,到了清代前期,仍然是帖学四家“翁刘梁王”的天下。可见历史的轮回跟社会文化的变革有着如此相像的地方。至于后来出现的崇碑的风尚,是因为清代中期乾嘉学派的出现跟当时出土文字的增加,使得大家在书写上发生了改变,所以清代后期出现了一大批碑学名家。刚才说到的沈曾植,那是位非常重要的、非常有代表性的书家。他的成功,固然跟他具有很好的帖学基础相关,但是他能把帖学笔法自然地跟碑学融合起来,打造出自己的一个天地,这才是最难做到的。
在此,我想提到于右任。对于右任从宗碑至中年后改学小草书的史实,我的结论是,如果于右任能延续他早年已经确立的书风往下走,不改弦更张地去接触所谓的标准草书,他的成就可能会更高。在创作借鉴上,先帖后碑和先碑后帖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用笔方法,当你在北魏书创作还未至相对稳定时便加入小草书一式,反会使笔法凌乱无序且显得不伦不类。我想,但凡从事书法创作的人,都会有这么一个客观的认识,就是对于右任晚年草书不甚认同,他的大量作品几乎都是在重复自己的有限技法,随着年龄的增加而日见老道。至于从艺术的高度上讲,当然是另一回事了。碑学书画从清代中期开始一直到清代后期,几乎形成了人人言碑的境况,写字的人如果不懂碑、不写碑,大家都会觉得奇怪的。像何绍基这么早出名的人,到中晚年也受周围朋友的影响开始写碑了,尽管这个碑写得未必怎样,但因为笔性好,倒也有他自己的风格。从某个视角看,碑和帖在高度融合以后,再加上当时社会环境,才会出现海派书法这么一种具有鲜明地方特点的书写类式。
吴昌硕 自作诗手卷 行书 钱君匋藏于“众美抱华——钱君匋的艺术世界”中展出
海派书法与市场的发展
刘一闻:大家知道吴昌硕是海派艺坛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的重要不仅是因为他能刻能书能写,同时他还感染了一大批人。吴昌硕的市场之庞大,从若干年后的文物商店、日本人大量购入他这一类风格的作品,就足以证明。我去过很多次日本,也跟当地书界的朋友有交流,即便是当地不太知名的书法家都能拿出几件吴昌硕的作品来,可见吴昌硕遗留下来的作品在日本的量是非常可观的。市场跟创作是相辅相成的,吴昌硕之所以有这么一个市场,最直接的因素是他在艺术上的高度,以书法为例,他最初学习的是邓石如,后又接近了杨沂孙,写得非常像,再后来又学了一点儿吴让之,似乎没碰过赵之谦,40岁上下学石鼓文,但是他始终没有脱离过大篆金文的临写,比如在他35岁所作的一件《篆书司马隃糜七言联》中,就曾发现大篆书体样式。其实,一直到他80岁时都在临摹各类金文。我们反观吴昌硕的艺术水准,跟他一生的勤奋,一生在艺术上的不断进取是有必然关系的。从另一个意义上说,他的后期石鼓文书法是对原始石鼓文的再创造。
鲍贤伦:首先,有市场是好事情。在清代,因为有盐商的推动,艺术品市场形成,“扬州八怪”的艺术成果得以体现,“扬州八怪”如果没有市场的推动,是不可能成名的,因为他们本是仕途不顺后另谋出路的奇异硕果。海派亦然,上海开埠后,市场发展,艺术品成为商品,达到了一个空前的机遇。在旧时代,画画写字是修身而不是谋生;在新时代,谋生需另辟蹊径,上海成为首选。一些外地的艺术人才想要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也到上海闯闯码头。市场提供了艺术家们在上海站住脚的机会,这也是上海能聚集众多艺术家的缘由。如吴昌硕首选苏州,但苏州的舞台和支撑都不够,因此他最终选择了上海。
对于海派问题,市场应该给予正面、积极的肯定。相比今天的市场,当时的上海市场有着不可比拟之处,再以吴昌硕为例,当时的市场允许他临习石鼓文、金文,临习的作品同样作为商品交易。现在市场上流通的作品,很多就是他的临习作品。吴昌硕曾言:“余学篆好临石鼓,数十载从事于此,一日有一日之境界。”他说每次临习都有不同的“境界”,而市场也认可这个观点。沈曾植的作品亦是如此,作品一会儿是学碑,一会儿学帖,但求字者“门槛踏破”(方言,表示求字若渴),不管他写什么都要,认为都是好的。在海派书法绘画中,很难找到非常差的作品,真金白银“逼迫”着他们,不允许马马虎虎,作品要精、要考究,这是海派文化的又一个特征。
反观现在的市场,在多年的空白之后,艺术品市场重新复苏,大家难免会跌跌撞撞。但只要市场正常,对艺术家的创作肯定是有益处的;如果市场再宽容一些,对于艺术家探索性的作品也给予接纳,那对书画家的负面影响会少之又少。
赵之谦 魏碑四条屏 80.7×36.5cm×4 江苏省美术馆藏
画家书法的丰富性
鲍贤伦:画家书法好,在那个年代比比皆是,画得好的基本上都写得好,甚至可以与书法家们抗衡,甚至比书法家更厉害。程十发、来楚生、唐云、陆俨少等,书法在当时就比书法家们更好。
在当时的海派,如果单纯只是写书法,那就要求作者的旧学基础非常好,或各有侧重,如考据、诗章等。如沈尹默自认为其诗可排第一,他的诗词整理起来约有1000多首。画家画得好,旧学养也都深厚,陆俨少、谢稚柳等都经过旧学养熏陶,他们除了书法,绘画等其他方面也不断给养着他们的书法。因此,如果一个画家字写得很差,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他们都知道在书法和绘画上的用功程度,至少是要同等的,可以一天不画画,但不能一天不写字。
这也给我们反思,今天的书法家,竞争对手不再是来自于和当年一样的中国画高手,而是和前辈们相比,我们整体的修养太弱了。
刘一闻:在上海画坛,陆俨少、唐云这一辈老先生,无论绘画还是书法,他们都旗鼓相当,如果有所偏颇,那么可能两者都不会好。就事论事,西洋画中比较多掺入中国画元素的刘海粟先生,他的书法和绘画其实都一般。为画者为书者,如果你的功力足够、艺术观念正确,那么你在创作上一定不会低。如果你能画能写,就会比单项创作要丰富;如果你能画能写还能刻,那么你的理解会更不一样,你的表现手法跟作品的感染力量会更加强。上海是一个文化集粹的城市,不管是哪个艺术门类,我们的前辈的确是厉害的。
海派艺术听上去有通俗的一面,但更有丰富的一面,这丰富的一面对我们从艺的人来讲恰恰是一把钥匙,它让我们能全面地认识书画艺术的具体风格和创作高度之所在。
吴昌硕与蒲华
刘一闻:人与人之间交往,书法会在不自觉中相互影响。吴昌硕和蒲华是很好的朋友,他们的关系与吴昌硕和王一亭很相似。王一亭在经济上给予了吴昌硕很大的帮助,吴昌硕在上海立足后,又给蒲华以帮助。蒲华虽然能画能写,但风格不讨众人喜欢,人称“蒲邋遢”,而且他画中有凄苦的味道。
鲍贤伦:蒲华和吴昌硕在师承上没有关系,但蒲华的处境给我们一个提示:在艺术市场,要生存得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市场有它的局限性,而作者的画法需要符合当时的审美。
(根据录音整理,有所节选)